伴随着ChatGPT的热潮,关于AI兴起之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几乎成了各学科最显要的议题,致力于新媒体研究的传播学也不例外。而在这场由AI引发的知识生产方式变革风暴中,数字传播研究更需要及时关注这一时代新议题。杜骏飞教授的《何以为人?——AI兴起与数字化人类》一文很透彻也很及时地回应了两个问题:AI兴起对人类交流的深远影响,在本质上到底是什么?那种被深度数字化的人类将向何处去?该文基于ANT(行动者网络理论)和他本人关于媒介—社会共同演化的讨论,将生物生命、数字生命、机器生命均列入“交往人”主体范畴,其关于“全景式交往的主体类型”概括精细而系统,极具启发价值。这一主体类型框架的价值或堪比泰格马克在《生命3.0》里提出的生命阶段说,文中关于数字化人类虚拟化、智能化、外脑化三种后果的讨论,有令人惊异的文化批判价值,而论文的学术主旨聚焦关于“何以为人”的追问,更是将这类专业化讨论引向了终极的人文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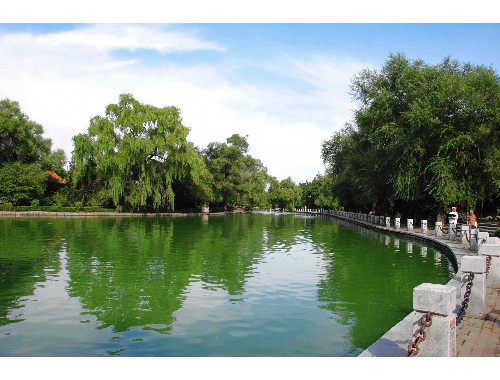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何以为人?——AI兴起与数字化人类
作者 | 杜骏飞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数字人类世”警示我们,正在发生的数字化历史中,人类或将为数字科技所控制。在AI兴起的时代,数字化的人类也包括智能辅助人、生理增强人以及非整数维度的数字人。类型学揭示了数字化人类的三种发展方向:一是虚拟化,二是智能化,三是外脑化;相关趋势分析也足以说明,技术可能加诸于人的支持力和支配力可以大到何种程度,而人的自我迷失又将产生何种后果。关于人在“数字人类世”中将何以为人的疑问,本研究的回答是:只有在葆有自由意志与道德良知时,人才可能继续为人,并在数字交往的空间里实现数字化的跃升。
在一个以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兴起为象征的AI革命时代,我们迫切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人类自身。置身于AI觉醒的前夕,人正转向一种新的技术形态:数字化人类。也因此,这里的问题便是:数字化人类何以可能?以及——人将何以为人?
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曾以“人类世”(anthropocene,也译为“人类纪”)作为一种过度技术化的现代性灾难的指称,又以“逆人类纪”(neganthropocence)一词作为人类努力逃离这一后果的指引,他“把海德格尔的座架(Gestell)和生成(Ereignis)概念理解为人类纪意义上的外在化,将生成理解为逆人类纪”。
这里,“人类世”其实是一个从自然科学那里借来讨论人类生存的哲学概念。地质学上,自260万年前以来是第四纪,第四纪又分为两个世,一个是从260万年前到一万多年前的地质年代,名曰更新世(pleistocene),一个是从一万多年前开始的地质年代(也是人类生活的地质时期),叫全新世(holocene)。气象学家克鲁岑(Paul Crutzen)及其合作者于2000年提出“人类世”这一术语,并试图说明:20世纪的许多方面都被人类活动所塑造,包括气候、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和水文循环等,这种人类活动在地质时间尺度(geological timescale)上留下了足够的印记,因此,应该将当前地质时代从全新世改为“人类世”。
“人类世”定义的本质,是要指涉地球环境危机;因其人类批判色彩,也引发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注。其间,大致的逻辑是:“人类世时代的地球是人类学的地球,需要地球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好的理由,不是吗?不过,也许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的解释更有抱负,他认为,“anthropocene”概念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人类、技术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框架,将人类纳入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中。
也因此,才有了斯蒂格勒等人以人类世为主题的技术哲学批评。涉及这一主题的,还有拉图尔(Bruno Latour)——他倡议说:“anthropocene不仅是地质学家在研究地球层序的过程中根据新的地层标志提出的概念,也是生态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必须考虑的概念。”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数字交往,连同当下被学术界与IT产业所追逐的虚拟现实、混合现实,元宇宙、Web3,脑机接口、AI革命,诸如此类的技术趋势正适于人类世的反思。因此,追随着斯蒂格勒、拉图尔那一代人的讨论,我提出过一种意见:如果地质学、气候学可以拿工业革命或核爆炸作为其“人类世”周期的起点,哲学界可以拿“人类世”一词发展为对技术时代的批判,那么,面向未来、现实—虚拟的数字化生存时代,或更有资格被视为一种新的人类周期。我称这一时代为“数字人类世”(digital anthropocence)。
在人的意义上,“数字人类世”之说意在告诫:人类正在发生的数字化历史,预示着人被数字科技所支配的危机;当实在的人类走向虚实相生、人机并存的数字化新人类时,不要只问数字科技何以可为,还要追问自然的人何以可能。
数字人类世一词,是沿用既有的概念而称之为“世”(epoch)的,可是,原本“人类世”这一命名法,是略显夸张了——地质分期通常以千年、万年、亿年为单位,在它面前,人类的全部演进史都很短暂,何况数字化这一新时期。即使将“人类世”当作哲学隐喻,也要考虑到其造词法的合理性。地质分期,从时间层级上来说,由高到低分别是宙(eon)、代(era)、纪(period)、世(epoch)、期(age)、时(chron),我以为,其中最小的分期“时”(chron)或切近题意——与它对应的地质“时带”,是没有特定等级的正式年代地层单位,其地理范围是世界性的,但它的可应用性只限于那些其时间跨度能够在地层中识别的地区。
有鉴于此,我其实更希望将这个人类数字化生存时期,称为“数字人类时”。不过,考虑到“人类世”这个词在哲学社会科学对话中已约定俗成,那就在本文中仍称之为“数字人类世”吧。
在数字人类世里,从好的一面看,人类的意识、生存方式、联结程度或将得到大的发展;而从坏的一面看,自我沉迷、虚拟依赖、AI崇拜,则会成为流行的数字文明病——倘若如此,数字未来在今天所需要的,就不能只是“加速”,还应该加上“警醒”。缺乏警醒的技术狂奔,或将被物的霸权所奴役,并难免要归于那种“人类世”的命运。关于人为技术所物化的本质,斯蒂格勒的表达是,“劳动者已经变成了机器的器官”。再高超的机器毕竟还是机器,再原生的人毕竟还是人。人演化为机器的器官,这是如何发生的?
我提供过一个解释:在数字交往化的语境里,人成为“交往的人”。在现实—虚拟的混合环境下,人对虚实的理解在数字技术的整合下逐步趋同,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思维、表达和行动方式也被数字逻辑“交往化”了——我曾把“交往化”定义为:人以数字交往为准绳建立时空联结、形成社会结构的过程。因“交往化”规则的反复激励,人趋向于成为深度媒介化的人,他们依靠数字技术的嵌入来获得生存资格,更通过被高超的技术力量所支配来建立生存优势;也因此,那种数字空间里的人,迟早也将成为更为常态的交往人,到头来,数字交往化的身份才是人的基本身份。
典型的数字人类世,是以人的交往效用而不是人的自身为第一性的。在那里,人显得更为功能化了,在时间、空间、心理的多重意义上,人的本体走向一种混同的定义,那些融入数字交往的人成为了“新人”:他们是被AI辅助的人;是生理意义上的增强人;甚至,是非整数维度意义上的数字人。
不仅如此,所有类型的数字生命(数字人、虚拟人、类似于ChatGPT那样的AI内容生成应用或拟人对话程序),以及AI加持的机器生命(仿人机器人、高仿人机器人),也将以智能化仿人的方式加入数字交往,并竞争交往人的身份。
基于ANT(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数字交往论的讨论,我对生物生命、数字生命、机器生命做了一个全景式交往主体的类型学设定——尽管本题仅讨论“数字化人类”部分(见表1)。
数字化人类是人类自身在深度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与并非基于人类自身的智能化仿人一起,建构了数字交往时代的主体性。
科学界曾将人工生命研究分为三类:软人工生命(soft artificial life,SAL)是指模拟生命过程的计算机程序和模型;硬人工生命(hard artificial life,HAL)是指构建物理机器来模拟生命过程;至于人工通用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则是指能够执行一般智能任务的人工智能系统。
在全景式交往的生命主体中,上述类型学对应着不同的组成部分:(1)HAL显然对应着仿人、高仿人机器人;(2)SAL对应着数字人、虚拟人,以及提供拟人化对话服务的AI——例如被视为内容生成神器的ChatGPT;(3)至于AGI,大部分主流AI研发都是要以AGI为发展方向的,开发ChatGPT的OpenAI如此,在科技观念上更为谨慎的DeepMind和Anthropic等也是如此。
无论是数字化人类(真人、智能辅助人、生理增强人),还是数字生命意义上的“拟人”,抑或是机器生命意义上的“仿人”,其背后都是以数字交往科技,尤其是以AI科技为支撑的。
ChatGPT这样定义自己:“一种基于大规模预训练的语言模型,使用了Transformer模型和无监督学习算法进行训练,可以生成自然语言文本,包括答案、对话和生成式文本。ChatGPT可以在多种语言和领域中应用,支持对话交互、智能问答、摘要生成、文本翻译、情感分析等多种应用场景。”
当前,ChatGPT在“交往效用”上已抵达内容生成应用的前沿,这是既往人机聊天程序所不及的高度。究其原因:(1)相对于以往的AI模型,Transformer模型能够产生更加流畅、连贯的回答,并且能够处理更加复杂的自然语言任务;(2)与同样采纳Transformer模型的竞争者相比,ChatGPT又采用了更大规模的语料库进行训练,使得它的语言表达能力显得更强——许多人是第一次在AI面前感到:它们在对话中开始像人了,而且是在更高的知识维度上。
对于深度数字化的一代新人来说,除了数字环境之外,AI将是他们重要的“交往人”,也许还会是最重要的。不仅如此,以AI的崛起为背景,人的自身也将被全面地改进——准确地说,这样的演进其实早已开始。
关于数字化人类,其“新人”或深度数字化的部分,在技术上可分为几个主要类型:
(1)生理增强人:主要由数字科技工程(如脑机接口、嵌入式芯片、数字义肢)增强生理的真人,可简称为“增强人”;当然,机械驱动、功能强化药物等也在增强生理工程之列,但不属于本题讨论的范围。
(2)人工智能辅助人:长期接受优势AI深度辅助的人,可简称为“智能人”。这里,为了衔接当下的学术对话,我们将智能辅助与生理增强作了区别讨论。严格来说,AI辅助也是一种(脑力上的)人类增强,即使设备并不嵌入到体质。不过,展望脑机接口技术的未来,起决定作用的芯片,其前景也将是AI赋能。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反对在非治疗情境下对人脑的外部控制,但显然,功利主义驱动很可能会导致AI嵌入人脑变得无法阻止。
(3)“真人数字人”:真人在数字网络系统中的数字生命,可简称为“数字人”。在数字交往时代,数字人是被系统所运行的“真人”。数字化的真人受数字空间秩序支配,假如DAO那样的政治乌托邦无法实现,那么系统、AI程序、超级经验体系(metaverse,或“元宇宙”)之于数字人,仍将有如君主。不错,交往的反抗在所难免,但在一个由技术权力造就的世界里,数字人有效的反抗最终也只能来自掌握科技的人。
虚拟人、数字人和拟人程序都被归为“数字生命”。数字生命可否称之为“生命”,在学术界还有争议。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数字生命是数字时代生命主题的新型表现方式,“以数据信息形式在数字空间中留痕,生命演化为‘一般数据’,以一种全新的无差别的虚拟数据作为生命的表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通过数字账号和数字语言加以显现,通过支配自我建构的数字账号联合他人形成不同的交往圈子”,从而推动构造主体生命的集合体,获取一种交往圈共在性。当然,另一方也提出了反驳,其中较为直接的,是对数字生命可否日常生活化的质疑。例如,凯文·B.克拉克(Kevin B.Clark)认为,机器架构、算法和社会网络并不能准确地模拟人类的认知过程及社会实践活动,难以真正与人类日常生活惯例相绑定,因此,数字生命也就难以被当作真正的生命形式。
认可是有价值的,而质疑也言之成理。毕竟,在数字生命的基本类型中:(1)虚拟人并不是“人”,也不在现实中对应具体的人,而只是具有数字交往意义的交往端;(2)数字人,作为非整数维度的“人”,尽管有真人的对应而具有化身身份,但毕竟在数字系统中也只是符号和程序;(3)与以上类似但更具争议性的是拟人AI程序——仅仅是因为它能对话或为人服务就可以被视为“生命”吗?
我认为,对数字生命的承认,并不是在指“数字物是人”,更不是在说明“生命不再是生物体”,而是在交往效用的维度上将特定的“数字存在”视同为生命,由此,自然地扩展了生命的外延。
我赞同数字生命(数字人,虚拟人,拟人程序)以“生命”为身份,有三个理论前提:(1)它必须是具有人格化意味的,而不仅仅是功能和工具的;(2)它必须是交往化的,而不是孤立的存在;(3)它必须是在体系中参与共同演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数字生命的类型中,虚拟人、AI程序都是智能化仿人,但它们在智能意义上可归于数字生命;只有数字人,因其有一半属于人的维度,可以泛称为“数字化人类”。现在,我们来以数字人类的尺度来观察一下这些类型:
(1)数字人。数字人代理着人,但作为人,又是非整数维度的一种中间品,是人与数字技术深度杂糅的亚种,它通常是代理某一真人的数字化身。真人的数字化身在某一尺度、某一场景或某一交往维度上对应着真人,例如“千喵”对应着易烊千玺,“迪丽冷巴”对应着迪丽热巴,“虚拟邓丽君”对应着已故歌星邓丽君,这些虚拟形象都是数字人,也都在代理某一真人的艺人身份。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这些数字化身尚不能与真人自己密切融合。不过,我们可以想见,在更强的数字经验体系中,真人必将有能力认证、拥有并参与操控自己的多个数字化身。那时,形形色色的数字化身才造就出分身交往的数字时代,并建立起分身认知的精神世界。
(2)虚拟人。一个虚拟人形式的主持人、歌手、棋手、学者、医生,往往因其在数字社会中被个性化了,并被赋予巨大的交往效能,因此也会具有某些人的交往特征。如早期的Siri、小冰,后来的虚拟娱乐明星们——全球第一个栩栩如生的虚拟模特韦比·杜基(Webbie Tookay),韩国的虚拟偶像Adam、Lucia、Cyder,中国娱乐圈里的虚拟艺人洛天依、柳夜熙之类,尽皆如此。其中,韦比·杜基被称为虚拟人中的完美出品,不是因为其相貌和身材参考了超级名模的外形,而是因为她可以紧跟潮流做出系统性的变化——无论是身材、发型、性格,都可以瞬间改变。其间的决定性力量,不仅是虚拟明星工厂中的技术神通,也体现着数字时代里那些不断扩展的人性。
(3)AI程序。现在看起来,Kevin B.Clark的那种对数字生命可否日常生活化的质疑,在拟人化的、开始处理自然语言对话的AI成功兴起之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ChatGPT只是一个GPT程序附带了成功的聊天界面,就连虚拟人、数字人的外观都不具备。然而,它此刻嵌入到人的生活可以达到如此紧密的程度,直至为许多真人的聊天者所不及;而且,看起来还在涌现某种“思考”的潜力。让我们设想一下,未来,当一种AGI通过定制化为你的个人生活提供个性化伙伴时,你的生活工作学习为它所支持、关心,你们之间具有良好的沟通效用和长期的交往史,并且,它自身还能随交往而同步演化——当此之时,它对你而言,难道不比一切陌生的、遥远的万物更具有生命感吗?
数字化人类也好,智能化仿人也好,二者都扩展了交往人的定性;而数字化人类以深度数字化、分身、AI辅助与增强,扩展了人何以为人的可能。我们会在不远的未来看见以下图景:(1)在科学界,智能人科学家、甚至AI本身将占据重要位置;(2)在大学的课堂上,教师将以AI程序或AI赋能的虚拟人为助教从事教学;(3)在公共场合,公众人物将以自己的多类型数字人投入日程运行,建立分身工作;(4)至于娱乐圈,也必然会出现“数字增强艺人”“明星数字真人”“数字虚拟艺人”的同台会演,当然,台上与网上,届时也将出现观众及其化身济济一堂的奇观。
数字化人类更为可感的部分,当然是人类自身——但是,他们很可能是受AI驱动的人,包括智能辅助与智能增强的人。看上去,智能辅助与智能增强是两个不同的主题,但在虚实相生、人机并存的环境下,其受AI加持的数字化生存本质是近似的。
首先是智能辅助问题。尽管未必进入体质层面,但AI辅助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人类增强。以往的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讨论是忽略AI辅助的,因为AI并未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如今,看起来新的时间已经开始了。
前述关于智能辅助人的定义中,有三个约束条件:长期接受、优势AI、深度辅助。其中,(1)长期接受,意味着AI辅助成为人的生活与工作常态;(2)优势AI,意味着AI辅助的结果,足以建立被辅助者的重要优势;(3)深度辅助,意味着AI辅助对于人的实践而言,并不只是参考性的,而是具有专业支配性的。
仍以ChatGPT为例——它的优势是文本生成,即AI根据提示编写“新的”或“自己的”文本,AIGC(AI generated content)被认为是继UGC、PGC之后的新型内容生产方式。ALGC“是从内容生产者视角进行分类的一类内容,又是一种内容生产方式,还是用于内容自动化生成的一类技术集合”。具有数据巨量化、内容创造力、跨模态融合以及认知交互力的技术特征。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坊间可见的各种AI作品,都是AIGC的展现。百度研究院曾预测,AIGC技术借助大模型的跨模态综合技术能力,可以激发创意,提升内容多样性,降低制作成本,并实现大规模应用。
百度对AIGC的预感,现在已经得到了印证:一种足够好的大模型能够促进内容创作、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与丰富度,能完成邮件、视频脚本、音乐、童话故事、诗歌、论文、笑话、文案等任务。甚至,它的应用场景也包括:开发聊天机器人,编写和调试计算机程序等。鉴于知识人类的主要生存手段之一是内容生成,因此可想而知,AIGC类产品将风行到何种程度。
在某些测试情境下,AIGC在教育、考试、回答测试问题方面的表现甚至优于普通人类测试者。这使得它有望成为席卷各领域用户的智能辅助应用。一项意味深长的调查显示,截至2023年1月,美国89%的大学生都在用ChatGPT做作业。同月,巴黎政治大学宣布,已向所有学生和教师发送电子邮件,要求禁止使用ChatGPT等一切基于AI的工具,旨在防止学术欺诈和剽窃。
另一方面,微软已经讨论在Word、PowerPoint、Outlook和其他应用程序中利用Open AI的技术,这些程序也将能根据用户提示编写整套文本。显然,这些广泛的应用将在改进语言生成、数据分析、翻译、知识调用、知识社交等方面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力。
迟早,AI压倒性的智能优势和交往效能,将使得AI辅助像数十年前的计算机辅助那样全面渗透人类行为——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日常生活。至于巴黎政治大学那样的AI禁令,迟早也会被AI融合所取代——想想计算器、互联网被发明后在课堂里的遭遇。计算器问世后,人们普遍提升了“计算”的能力,但计算的竞争并未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更高水平的数学学习问题;同样,互联网问世后,人们普遍提升了存储、查询、传输信息的能力,但信息的竞争并未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更高水平的信息利用问题。
2023年2月4日,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Isaac Herzog)发表了部分由AI撰写的演讲,成为首位公开使用ChatGPT的国家领导人。这其实是一个适切的寓言:假如总统可以使用一个真人辅助撰写演讲稿,那为什么不可以使用AI辅助呢?假如一个总统可以使用AI辅助来工作,那么,一个学生为什么不可以使用AI辅助来更好地学习呢?只不过,当教学与AI辅助互相渗透时,其间的学习、培育、评定、考核模式将发生怎样的调整,人们还不确切知道而已。
AI辅助作为一种技术史的趋势,将蔓延进人类的精神,并逐步汇入一种主流化的数字文明,而这种文明将默认:AI是一种基础设施,人们对AI的一切考量、一切修正、一切批评都是以接纳AI为前提的。
也因此,智能辅助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普遍的,它意味着人类的自我迭代出现在崭新的领域,由于外挂了AI的知识调取利器,人在智力的表现(当然,也仅仅是表现)上与他们的祖先已经迥然不同了。我判断,关于AI辅助的方式,可能会随着技术的成熟,不断分化及场景化,包括但不限于:(1)从搜索对话到自动辅助;(2)从手机和电脑到可穿戴载体;(3)从外部设施到脑机芯片;(4)从个人服务到环境设施支持;(5)从独立计算到联结运行。
有学者认为,凡以自然的或者人工的方式(特别是通过某种技术手段)暂时或永久地克服人体局限的技术展现形式,都可归为“人类增强技术”(田海平,2021)。以我之见,如果以虚拟—现实、AI、脑机接口、基因工程等基础技术革命作为指标来判断,未来最重要的人类增强,并非是对人体局限的克服,而是对人自身(复杂意识、生存竞争力、交往效能)的扩展,以及对人的更高愿望的满足。
也因此,“数字人类世”里的人的变革,并不只有深度数字化的“新人”、AI附体的仿人,还有源远流长的另一个方向——以技术改造人,将人嵌入技术工程的增强人。
增强人类的知识学源头,从神话时代就开始了。在西方,是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英雄——半神(demigod),是神话中的种族,众神们经常下界来到地上与凡间女子生子,其中,宙斯是最出名的。神与人的后代都会有一半神的血统,可是他又不具备神的资格,所以被称为半神。例如,宙斯的两个儿子都是半神,一位是历经劫难、修成善果的珀耳修斯(Perseus),另一位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而在中国神话中与之对应的,则是形形色色的“感天而孕”——所谓“圣人皆无父,感天而应”。譬如开创易理的伏羲,他的母亲华胥氏是因以足丈量巨人足迹受孕。教人医疗与农耕的神农氏,他的母亲少典妃女登是感神龙而孕。而被中国人尊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他的母亲附宝则是因见一道电光环绕北斗枢星,感应而孕,怀胎24个月后才生下黄帝。大约,在原始思维中,人也只有得到神的血缘加持,才可能生而神灵吧。
对于异种因素加持人的体质,人类始终有美好的想象,这与人对更高演化的追求应该是一致的。
至于增强人的现代思想,则来自赛博格(cyborg)概念。cyborg是cybernetic organism之义,表示生理功能受电子机械支配的生物有机体(包括人),也通常被理解为电子人、机械人、义体人、改造人。这一概念由两位工程师于1960年在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所做的报告中首先提出,其初衷是要通过机械、药物等技术手段来增强宇航员的身体性能,以适应外太空生存。
就当下科技而言,人类增强工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数种:基因编辑、外骨骼与可嵌入设备、电子义肢、药物增强(记忆改善、心理控制与寿命延缓等)、容貌医学,以及这里要讨论的脑机接口。其中,有一部分项目,其初期产品就已被人类所适应,例如电子义肢、医美、药物增强,而另一部分项目则正在发生重大的进展,例如外骨骼,以及脑机接口(BCI)。后者,是我们在这里要聚焦讨论的部分,因为它有望制成更具想象前景的增强人。
脑机接口,是指在人或动物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的直接连接,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换。如果是双向脑机接口,则允许脑和外部设备间的双向信息交换。其中,外部设备指任何可计算设备——从简单电路到硅芯片,直至我们正在讨论的智能机器。
在关于增强人的伦理学争论中,脑机接口并不是一个显赫的议题。其主要原因是,对脑机接口的研究已持续了超过40年,其医学初衷是恢复损伤的听觉、视觉和肢体运动能力,而非增强普通人。现在,我们在本题之下讨论脑机接口,起因是马斯克投资的Neuralink展现了更多的增强可能。该项目的主体,是要往人脑中植入微芯片——它能够记录大脑活动并施加某种刺激,在人脑和AI之间实现“共生”(symbiosis)。2020年,Neuralink成功将大脑芯片植入一只猪的脑中,并在两个月后的路演中,首次向外界展示了位于猪脑中的芯片如何实时向外部传送数据。2021年4月,Neuralink的技术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它向外界展示了一只猕猴如何凭借意念来玩电子游戏。可以想见,在人脑中实现这类工程设计的目标也将触手可及。
一般来说,脑机接口通常给予病人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而不是让人被动接受外部世界的控制。但这种单向控制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技术上,反向回路的控制同样可行——视觉假体、人工耳蜗等感觉修复技术即是如此。
在双向脑机接口技术的支持下,那种关于外部计算设施控制人脑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处在计算中心的人、机器或程序,可能出自某种目的,通过脑机接口支配人的感知或思想,且完全可能的。
一种技术在其成熟之后,总会向其可推广的领域蔓延——只要它有功利效能。有人预见,未来当脑机接口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将不但能修复生理残疾,也能增强正常人的功能。例如深部脑刺激(DBS)技术和RTMS等技术,既然可以用来治疗抑郁症和帕金森氏病,将来也可能可以用来改变正常人的一些脑功能和个性——实际上,海马体神经芯片已被论证可以用来增强正常人的记忆。
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非治疗性的芯片增强,是服务所有人的,还是服务少数人的?另一个问题则更为敏感,这种非治疗性的芯片增强,会有哪些政治、文化、商业、军事、教育、法律的利用?如果脑机接口是一个如此便捷的控制人的通道,将会引发哪些更为深远的企图?
这就是关于交往人的最大哲学危机,BCI-AI的整合可能使人成为一种外脑化的生命。
马斯克表示,长远来看,Neuralink的大脑芯片可应用于人类意识与AI的融合工程。这看起来很矛盾,不是吗?一方面,马斯克对AI疑虑重重,认为它是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另一方面,他提供的解决方案则是要在人类最脆弱、敏感、重要的器官深处实现人与芯片的融合。
我不怀疑人与AI的共生是一种未来的趋向,但脑机接口与强AI的具身联结,恐怕并非智能协作那么简单,以当前的AI水平来评估,人类在知识、智力和记忆方面已远远落后于AI,何况未来?我也并不怀疑大脑芯片将帮助瘫痪病人重获数字自由是一种科技福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担忧操控者在健康人身上滥用这一神通。
将BCI与AI技术相结合,的确可以产生许多有用的应用,尤其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控制智能设备,或开发新型的智能辅助工具。但它也存在强烈的风险和挑战,例如:(1)隐私和安全问题,使用BCI和AI技术进行脑波信号的解析和分析可能导致他人利用这些技术来窃取个人的脑电信号;(2)道德和伦理问题,使用BCI和AI技术来操纵人类的意识和行为,导致人类自由意志和自主性的受损,以及个人意识的削弱。
前述关于智能辅助人的定义中,有三个约束方向,恐怕我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当智能人同时在这三个方向上走向极致时,那就必然是类似于BCI-AI的嵌入式智能增强。这样,AI辅助的人,即有望成为终极意义上的增强人——毕竟,没有什么增强比外脑化更石破天惊。
此刻,我们还没有一份关于人类AI增强的风险日程表,但我确信,当BCI-AI时代催生外脑人的那一天,会有一场劫难——无论外脑人多么智能,他都会因为失去思想自主性而无以为人。
总结而言,关于人类增强问题,我有如下意见:(1)如果按照“更高愿望的满足”之说,或许,在机体哲学认识论的意义上,未来最重要的人类增强,将因为人类欲望的增强而更接近不合理的技术滥用。(2)有学者指出,人类增强有“兴奋剂模式”和“疫苗模式”之别——前者是着眼于机体个别机能或局部机能的提高的人类增强技术,后者是着眼于提高机体自身的整体机能。不过,谁能确定局部机能改善就是不合理的人类增强呢?人类几乎所有医药科技的进展都是着眼于人体局部机能改善的,却从未有人指责过医药属于“兴奋剂模式”。因此,我所期待的,并不是要确定某一模式的增强,而是要就每一种增强技术的具体应用,诉诸生命伦理及公平正义。
西蒙·娜塔莉(Simone Natale)等人提到:将数字计算机视作思维机器(thinking machines)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早期很常见,他们对此视为一种关于AI的现代迷思(modern myths)。通过对《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两本杂志中人工智能相关文章的内容分析,作者总结出了建构人工智能迷思的主要模式,其中包括:(1)类比和话语迁移(discursive shifts)的再现,即将其他领域的想法和概念用于描述AI技术的功能;以及,(2)对未来的修辞运用(rhetorical use),即设想当前的缺陷和局限性将很快被克服;等等。
对这两种模式,我们感到很熟悉吧?是的,因为它们是今天仍在流行的论点。随着“元宇宙”、web3.0、AI等技术热潮的次第来临,我们这个世界总会回响起似曾相识的技术乐观主义的声音。仿佛只需新技术革命的一个转身,先进而丰饶的理想世界就将诞生。而实际上,围绕着技术跨越的哲学反思是异常复杂的,也是险象环生的,往往需要人有更多的审慎。
在这个AI觉醒的前夜,我们不得不以更为强大的物为背景来思考人,也不得不以数字科技,尤其是AI来衡量“人”。
根据本文的讨论,数字化人类存在三种发展方向:虚拟化、智能化、外脑化。这三者大致说明了,技术可能加诸于人类自身的帮助、影响可以大到何种程度,以及它对人的支配力将如何令人震惊。
在《奇点临近》一书中,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认为,人工智能很快就能囊括“人类所有的知识和技能”,一旦有了纳米尺度的脑扫描技术,我们就能“逐步将自己的智力、性格和技能转移到非生物的载体上去”。这是一种典型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本质是“把人类当前阶段看作是进化过程中的过渡阶段”,然而,其后果,恐怕正如凯利(Kevin Kelly)在《失控》中所说:“造化所生的自然王国和人类建造的人造国度正在融为一体。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
一个机器渐渐人化的世界或许是可喜的,然而,一个人逐渐物化的世界却是可悲的。广义来说,一切有关数字人类的乌托邦叙事,都是与人类自身演化欲望有关的——很明显,人可能意欲在科技加持下走向超人,而其结果却是走向非人。
按“复杂意识扩展”之说,我仍然主张人与技术、社会、环境之间是共同演化的,人不可能脱离生态系统单独进化,也不可能在系统进化后独自留在原地。一方面,“后人类主义”洋溢着技术乌托邦的激情,这种激情在历史上往往过激;另一方面,恐怕我们也很难否定:人这一物种仍处在漫长的演化之中,并仍将需要在身体、技术、功能上取得进展。
如前所述,那种意识复杂化的人,以及被数字技术“交往化”的人,既是技术的演化,也是新人的初生。在数字人类世的历史语境中,如果说,机器觉醒必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那么,我希望人类也能在认知、伦理上取得与科技相称的进展,因为对科技的善用而走向新生。
因此,关于数字化人类将何以为人,我的答案是:当人的自由意志始终能支配数字人类世,人不因物的崛起而失去人性时,我们将继续为人,并在数字交往的空间里实现数字跃升。
本刊坚持原创,欢迎转载
版权所有,如转载,请注明:
本文转载于南京社会科学
欢迎个人转发
媒体转载请联系后台授权
投稿网址:http://www.njsh.cbpt.cnki.net
联系电话:025-83611547


